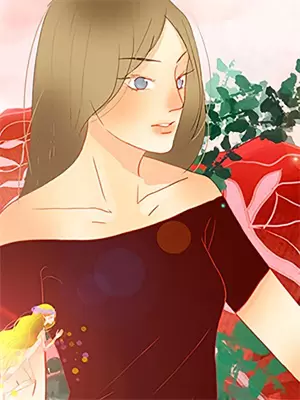第一章 夜车不告而拿,叫偷。 我常坐夜班车,像偷别人的睡。车里空,灯发白。
一路只剩我和一个女人。她靠窗坐,手紧紧拽着包,像要把什么压住。司机不说话,
车像一条钝刀子,慢慢划过城。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她的侧脸。瘦,没血色。
眼睛像熄火的炉子。她不看我,也不看窗外。整趟路,她就像在等判决。我也不说话。
我习惯沉默,喜欢听车的响。轮胎压过井盖,砰一下。
我注意到后门上方的摄像头红点时亮时灭。女人抬了下头,似乎在数那红点。数到第五下,
她忽然停住,手更紧了。司机的后视镜里晃过我的脸。我避开,又忍不住看他。手粗,
指关节白,握得稳。红绿灯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那一眼擦过我和她,像把钢尺,冷。
车往城北,越走越空。终点站前,女人按铃。清脆一下,像针。她走到后门,站着不动。
车停,门开,她也不动。门嘶一声合上,她才忽然跨出去了。动作不大,
却像拔掉了一根钉子。我多看了她背影一眼。细,像被风折过的纸。她没有回头。车起步。
我没下。我想再坐一圈,想再确认她去哪。可我胃里忽然翻一下,像被什么碰了。我按铃,
下车。站牌下只有风。天还没亮,摊位冒出灯光。我去买早点。豆浆热,油条硬,我咬不动。
没胃口。我把杯口贴在唇上,却没有喝。我等,等一双鞋踩到地上的水印,
等那双鞋的主人开口。他来了。司机。黑外套,拉链半拉。肩上有白粉,
是站里墙皮掉的那种。他点了根烟,又灭了,似乎怕别人看见他抽。我喊了他一声“师傅”。
他抬眉:“又见面啊。”我笑,说夜里清净。他点头,说清净。他的“清净”里有疲惫。
我盯着他的喉结上下动,心里怪安静,又怪吵。我问:“车上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他顿了一下。很短。一闪,就是那种一秒里头塞了十几层话的顿。他把纸杯往手心捏了捏,
像在确认热度:“哪个女人?”“靠窗的。黑外套,眼睛很……很深的那个。”他看我,
像第一次看见我:“没看到。”我本能地点头,像是他讲了一个合理的答案。
可我的后颈当场起了一层小疙瘩。没看到?我把她的坐姿、她的手、她按铃的那一下,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每个细节都真得发冷。怎么会没看到。“可能我看错了吧。”我说。
他“嗯”了一声,低头喝了一口豆浆。很烫,他没皱眉。像吞下去的不是热,是别的。
我们没再说话。摊主在剁咸菜,刀一下一下,像车过井盖。天慢慢亮。路边垃圾车开过来,
压出一股酸味。司机抬手跟熟人打招呼,笑了一下。笑很浅,很快,又收回去。他看了看表,
说要回场站。“慢走。”我说。他走了。我没动。我把凉下来的豆浆一口喝干,
心里空了半寸,像被撤走了一块砖。我回家,鞋底带着摊位地上的油。我躺在床上,
却睡不着。女人的背影在眼前晃。司机说“没看到”的那个顿在耳边钉着。我闭眼。
耳边是夜车的气门声。那声音细,又长,像有人在门后磨刀。磨给谁用,不知道。我翻身,
把脸埋进枕头。过一会儿,我起身,洗了把脸,像从水里拖自己出来。我又去了那条线。
车号没变,司机没变,座位没变。我坐回昨天的位置,后门上方的红点还在跳。
我盯着那红点,数到第五下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像有人在我背后轻轻碰我。她没上来。
车走完一圈,天色暗下来。我不甘心,再坐一圈。第二圈中途,一个站台边,她上来了。
黑外套,头发湿,像刚从雨里穿过。她走过我身边,风一动,带出一点洗衣粉味。
我吸了一下气,喉咙紧了。她仍然不看我。她坐回昨天的位子,靠窗,手抱着包。车过桥,
灯影在她脸上划出一道又一道。我想起早上的摊位,刀起刀落,剁咸菜。她的眼睛没有焦点,
但我知道她在看玻璃,或者玻璃外面的黑。我从裤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捏在指腹,指节发白。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是在等。等她眨眼,等她叹气,等她给我一个证据,
让我证明她是真的在这儿,或者不在。终点站前,她再次按铃。还是那一下。清。
她站到门口,门开,她不动。司机这次回头,眼角扫她一下,又看路。他没有说话。门关上。
她往前迈了一步,像迟到半拍的音符,滑出门缝。我没有立刻下车。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站牌后。像一滴水掉进黑里,不起浪。我跑下去,追过去。
站牌后是空地。空地后是围墙。墙上贴着一张旧告示,被雨泡得发白,字糊成一团。
风把纸的一角翻起来又甩下去。地上没有新鲜的脚印,只有旧的鞋印交叠成泥。
我退回到灯下,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她走快了。她绕到另一条巷子。她打车了。
她本来就不该在这儿。背后传来发动机低声,车要回场站。我回头,看见司机探出半个身子,
朝我摆手:“回不回?”我咽了一下口水,跳上去。门关上。我站到他身边,隔着护栏。
他侧头:“又来一圈?”“最后一圈。”我说。他说好。他抬手拨了一下后视镜,
把镜面对准后门。我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苍白,眼圈黑。我侧过头,看见他手臂上的青筋。
他手握方向盘,指背的骨节像小石头。我忽然觉得很饿,又忽然觉得胃在缩。出站的时候,
我问了一句:“你真的没看到她?”他没有立刻答。他看了看后视镜,又看前方。红灯,
车停。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松开一点,像把一个重物放到地上:“没看到。”他语气平,
像陈述天气。我盯着他的嘴角,想从一个字里抠出别的意思。没有。他复又握紧方向盘,
灯绿了,车起步。他加了一点速,像要把什么甩掉。我不再问。我靠在护栏旁,
听车身每一下轻微的颤动。那颤动从地板传到脚心,再传到小腿。我忽然明白,
我要做的不是问。我要把答案从别的地方“拿”来。拿来,就是偷。
我决定明天早上再去那家老旧便利店。那里监控坏了一半。柜台下的抽屉总是半开。
昨晚我看见一种东西,亮,细,轻。它适合放在口袋里。适合握在手里。
适合让我靠近一个答案。我下车时,司机说了句:“早点回家。”我“嗯”了一声。
风把我脸吹得发紧。我走了几步,又回头。他没看我,眼睛盯着路,像在盯一条看不见的线。
车灯打在地上,割开一块亮。我站在那块亮的边缘,脚尖差一点进去,又收回。回到家,
我把门反锁。屋里冷。我把衣服脱下来,又穿回去。我躺着,睁眼到天亮。
眼前总是那一下:她按铃,门开,她不动。像有人在门边等我开口,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我把被子拉到下巴,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反复、清楚,又轻——不告而拿,叫偷。
明天,我去拿。第二章 便利店我睡了一天,醒来时,光线昏沉。屋子里闷,
我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砖。昨晚的女人像钉子,越敲越深。我想把它拔出来。
办法只有一个——再去坐车。晚上,我又去了那条线。车还是那辆,司机还是他。我上车时,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装作平静,投了币,往昨天的位置一坐。后门上的红点还在闪,
像一只小眼睛。它让我不安,也让我兴奋。我知道自己在偷别人的生活,偷别人的轨迹。
我在车上待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车开得慢,像故意磨。天色暗下来,
街上的灯零零碎碎亮起。我靠着窗,数过往的行人。数到第十个时,
车停在一间老旧便利店前。我忽然心动,下了车。便利店招牌掉了一半,灯管时亮时灭。
推门进去,没人。空荡荡的架子上,零食落着灰。收银台无人看守,柜台下的抽屉半开,
像一张张开的嘴。空气里有股霉味,又混着糖的甜腻。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偷点东西吧。不是饿,不是需要,只是那股冲动像刀子在顶着。
想偷,必须偷。我走到柜台,手伸进去,摸到一把水果刀。刀不大,塑料柄,薄刃。冰凉。
拿在手里时,我心里安静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抓住了某种秩序。偷来了就属于我。
偷到就是我的道理。我把刀揣进口袋,转身要走。门口的灯闪了一下,忽然,她站在那里。
昨晚的女人。黑外套,湿发贴在脸上。她死死盯着我,眼睛里没有情绪,只有冷。
我心口像被锤了一下,脚步乱了。她没说话。我也没敢说。气氛像被拧紧的绳子,随时要断。
我下意识加快脚步,擦过她肩膀,推门出去。门后风一吹,我背全是汗。我一路快走,
直到听不见门上的风铃。心里乱,像有人在耳边低语。我想回头看看她有没有跟上,
可我不敢。脚像灌了铅,每一步都硬。我拐进一条小巷,停下喘气,四周空无一人。
只有一只猫从垃圾桶里钻出来,叫了一声,尖细,像笑。我回家时,天完全黑了。
屋子里更冷。我把刀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刃子反射出一点点光,像一只眼。盯着我。
我用手指轻轻抚过刀刃,指尖一凉。那感觉让我心里发热。热得像要烧穿胸口。
我忍不住想:她为什么盯着我?她是不是也在偷?偷我的动作,偷我的秘密。
她是不是知道我偷了刀?她是不是要告诉司机?想到这里,我胃里又翻腾。司机。
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看我?我闭眼,却看到他握方向盘的手,骨节凸起,青筋如蛇。
那双手,我想抓住,想按在我身上。想让他属于我。可我越想,他就越远。远到让我愤怒,
远到让我想撕裂一切。桌上的刀安静躺着。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字。偷。偷东西,偷人,偷命。
想到这,我忽然笑了一下。短,轻,却把自己吓了一跳。笑声像从喉咙里被掏出来,
不像我的。夜深了,风从窗缝灌进来。我关了灯,屋里漆黑。刀还在桌上。黑暗里,
它亮一下,像一颗牙。我盯着那牙,直到眼皮沉下去,心里反复有一个声音:偷了,
就属于你。第三章 司机的故事第二天傍晚,我照例去了车站。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虽然从未说出口,但我知道,他会在那里。车来了。
车头灯一亮,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司机还是他,背挺得直,手稳。他看了我一眼,
像确认了什么,又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上车,投币,走到后排。今天车里多几个人,
但他们都不重要。他才是。我盯着后视镜。镜子里,他的眼睛偶尔扫过。每扫一次,
我心就被针扎一次。痛,又带点快感。夜深,车渐渐空。最后只剩我,他,还有红点的闪烁。
终点站,他熄了车,靠在椅背上。我走过去,说:“师傅,抽根烟?” 我不抽烟,
但我知道他抽。他愣了一下,从胸口掏出一包皱巴巴的,丢我一根。我点火递给他。
他吸一口,眼睛眯起来,白雾飘在脸前。我试探:“昨天的那个女人……你真没看到?
”他笑了一下。那笑淡,带着讽刺:“你是不是撞邪了?”我盯着他的脸,不动。
他沉默几秒,忽然说:“她死了。”我一震。他继续:“几年前的事了。
她是我场站里的女人,跟我不清不楚。后来闹得厉害,她喝了药。死在车场厕所里。
你要是晚上见到她……那就是她还在缠我。”他吐出一口烟,眼神冷下去:“她不肯走,
总觉得我是欠她的。可我欠她什么?我早说过,我不要了。”他说得平淡,
却像用石头砸在我心口。女人死了?可我清清楚楚看过她,黑外套,湿漉漉的发丝,
冷冷盯着我。“你不信?”他看着我。我摇头。不是不信,而是心里一团乱。
他盯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算了,你别管这些。夜车多怪事,见怪不怪。”他掐灭烟,
准备启动车。我盯着他手背青筋的起伏,心里烧起来。我想伸手抓住那只手,想把它偷过来,
藏起来。让他属于我一个人。可他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别老想她了。她是个疯女人,
死了也不安生。”疯女人。死了。缠着他。 字字如钉。我咬着牙,指尖压得发白。
我的喉咙里冒出一个声音: ——她是真的死了吗?还是你希望她死?我没说出口。
我只笑了一下:“哦。”车开回场站。我下车,走进夜色。风吹得冷,我把手插进口袋,
摸到那把水果刀。冰凉的刃贴着指腹,让我心安。偷来的东西,握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