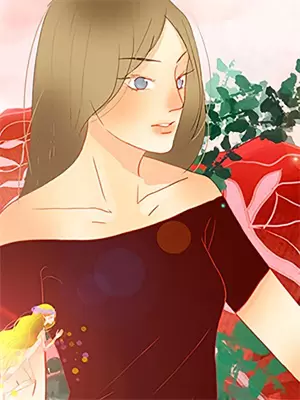文件是周二到的,牛皮纸信封,落款是县拆迁办公室,
印着“红溪村祖宅拆迁紧急通知”几个刺目的红字。末尾那句“限期七日,
逾期强拆”像淬了毒的针,扎得我眼皮直跳。三十年,那宅子像块沉进时间淤泥里的铁锚,
锈死了,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碰。可它到底拴着你,冷不丁一拽,五脏六腑都跟着生疼。
当晚我就上了最后一趟长途班车。车破路烂,颠簸得像在筛糠,窗外是泼墨般的夜,
偶尔几点孤灯,鬼火似的浮过去。邻座老头鼾声震天,我却手脚冰凉,胃里拧着个疙瘩。
闭上眼,总能嗅到老宅那股子味道——阴湿的木头、厚厚的灰尘,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甜到发腻的霉味,像搁久了的供香,渗进每一根椽子里的陈腐气。
天蒙蒙亮时到了镇子,还得搭一程拖拉机才能进山。开车的汉子听说我去红溪村,
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含糊吐了句:“那地方……邪性。”就不再言语,只把车开得快要飞起,
卷起一路黄尘。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枝桠虬结得像鬼爪。树底下蹲着个人,
“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是村长福伯。他老得几乎缩了水,脸上褶子堆垒,看见我,
混浊的眼珠动了动,烟杆“啪嗒”掉在地上。“阿……阿衍?”他嗓子嘶哑得厉害,
像破风箱,“你……你真回来了?”我点点头,没说话,只想绕过他。他却猛地扑过来,
枯柴似的手死死攥住我胳膊,力气大得惊人:“不能去!那宅子!不能进啊!”他眼球凸着,
血丝密布,恐慌几乎凝成实质,“要死人的!真的会死人的!听伯一句劝,快走!现在就走!
永远别回来!”他手指冰凉,那股寒意顺着胳膊直往我心口钻。我用力甩开他:“福伯,
我家房子要拆了,我总得回去看看。”“那不是房子!那是……”他猛地刹住话头,
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像是怕极了某个称呼,最终只是重复,
“不能进……不能……”我不再理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踩着荒草蔓生的小路往村里走。
身后,是他压抑不住的、像被掐住脖子似的呜咽声。村子静得可怕。几乎是死的。
几间土坯房歪斜着,门窗黑洞洞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连狗叫都没有。
只有风穿过破败屋檐的呜咽,一阵阵刮得人脊背发凉。祖宅就在村尾,孤零零一座。
比记忆里更破败,青砖院墙塌了大半,露出里面灰黑腐朽的木骨。两扇厚重的木门漆皮掉尽,
布满虫蛀的小孔,门上贴的符纸早已褪色发白,被风雨撕扯成几条残缕,
却还在风里簌簌地抖。空气里那股熟悉的甜霉味更重了,沉甸甸地压下来,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站定,深吸一口带着腐朽味的空气,伸手去推那扇门。
“吱呀——”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像是垂死者的叹息。
一股积攒了三十年的、冰冷彻骨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吹得我汗毛倒竖。就在此时,
身后——“啊——!!!!!”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尖叫猛然炸响,几乎撕破这死寂。是福伯,
他连滚带爬地追了过来,此刻却像见了鬼一样,手指颤巍巍地指着我背后,
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脸上是彻底崩溃的惊骇:“人!一个人!趴……趴在你背上!
!红……红色的嫁衣!女的!她……她回头看我了——!!”我猛地回头。身后空荡荡,
只有断墙残垣和呜咽的风。肩膀上什么重量都没有。但就在那一刹那,
我颈后掠过一丝冰冷的、非人的触感,像是一缕极细极凉的头发扫过,带起一片栗粒。
福伯“扑通”一声瘫软在地,裤裆瞬间湿了一片,腥臊味混在风里。他像是被抽走了骨头,
只剩下喉咙里“嗬嗬”的抽气声。我这辈子没听过那样凄惨绝望的嚎哭。
还没等我从那声尖叫和颈后的冰冷中回过神,杂乱的脚步声和哭喊声就从村子各个角落涌来。
男女老少,几十号人,像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踉踉跄跄地冲向我家的院落。
他们脸上是全无血色的恐惧,瞳孔放大到极致,有些人跑丢了鞋,
被碎石割得满脚是血也浑然不觉。冲进院子,“噗通”、“噗通”,
像下饺子一样朝着那黑洞洞的堂屋门口跪倒一片,疯了似的以头抢地。“祖宗饶命!
老祖宗饶命啊!!”“不是我们!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只是听了吩咐……只是帮凶……饶了我们吧!
着回来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哭嚎声、磕头声、语无伦次的哀求声和诅咒声搅成一团,
在这破败的院落里冲撞回荡,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他们磕得额头见了血,
浑浊的血水和眼泪鼻涕糊了满脸,癫狂而绝望,对着那空无一物的老屋,
如同跪拜一尊无形却足以顷刻间碾碎他们的邪神。我僵在门口,像被钉在了原地。
冷意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帮凶?祖宗?饶命?
这些破碎的字眼和眼前癫狂的景象搅拌在一起,在我脑子里形成一股恐怖的漩涡。
风似乎更冷了,那股甜腻的霉味里,仿佛真的掺进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
混乱持续了不知多久,才在几个稍微清醒点的老人连拉带拽、近乎虚脱的劝慰下渐渐平息。
村民们被搀扶起来,一个个面如死灰,眼神躲闪,不敢看我,更不敢看那宅子深处,
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逃散了,留下满地狼藉和一片死寂。福伯被人架着,
临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空空洞洞,只剩下纯粹的、被榨干了的惧怖。院门大敞着,
像一张沉默的、噬人的黑口。我站在那儿,午后的阳光竟然一点温度都没有。
手脚冰冷得不像自己的。背后?我猛地再次回头。什么都没有。
但那种被什么东西贴着、窥视着的粘腻感,却挥之不去。
我在村里唯一还开着门的小卖部买了把最大的手电筒和几节电池,
还有一把看起来还算结实的柴刀。店主是个眼神浑浊的老太婆,收钱时手指冷得像铁钳,
全程不敢抬头看我。我必须进去。拆迁文件揣在兜里,像块烙铁。而那些村民的疯狂,
福伯的尖叫,还有颈后那缕冰冷的触感……这一切都像无数只手,把我往那扇门里推。
深吸一口气,拧亮手电,握紧柴刀,我跨过了那道门槛。灰尘像雪一样厚,踩上去软绵绵的。
光柱扫过,蛛网密布,到处都是倒塌的家具和散落的破烂。
每一声细微的响动都让我头皮发麻。堂屋正中央,似乎曾摆过香案,
如今只剩一地碎木和烂布。我没有停下,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
走向父母生前居住的后堂卧室。就是那里,似乎总散发着更浓重的阴冷和甜腻味。
卧室的地板已经烂透了,手电光往下扫,能看到下方黑黢黢的空间。地窖?
我用柴刀劈开腐朽的地板入口,
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极致的阴冷、陈腐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腥臭的气味猛地喷涌出来,
呛得我连连后退,胃里翻江倒海。强忍着恶心,将光柱投向下方。光线刺破黑暗。
首先看到的,是惨白的一角。然后,一具,两具,三具……整整九具。
扭曲、蜷缩、相互叠压着,塞满了这狭小的地窖。尸身早已干瘪腐败,
裹着破烂不堪、颜色晦暗的红布片,像某种被遗忘的、丑陋的祭品。我的呼吸彻底停了,
血液冻结在血管里。手电光剧烈地颤抖着,
扫过那些空洞的眼窝和咧开的、露出黑黄牙齿的颌骨。最后,
光斑定格在其中一具尸骸的颈部。那里挂着一块腐朽发黑的木牌。上面刻着字。
我像是被魇住了,鬼使神差地,探身下去,用手指拂去上面的污垢。是我的名字。旁边,
是我的生辰八字。丝毫不差。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炸开,瞬间冰封了四肢百骸。
“……嗬……”极轻微的一声,像叹息,又像是女人哽咽的尾音,贴着我耳根子吹过。
手电筒“哐当”一声砸在地板上,滚了几圈,光线徒劳地切割着黑暗。我在绝对的黑暗中,
一动不动。能听见的,只有自己心脏疯狂擂鼓的巨响,
和那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的冰冷注视。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时间碎成了粉末。
黑暗浓稠得像墨,裹着我,往深渊里沉。那几声呜咽,那缕寒气,是不是真的?我不确定了。
什么都确定不了。只有冷,骨髓都要结冰的冷,还有那股甜腻的腐臭味,它钻进来,
糊住了我的口鼻,我的脑子。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是永恒。
我动了动僵硬的手指,摸到滚落的手电,“啪”,光又亮了,刺得眼睛生疼。
我不敢再看地窖里那九团模糊的白,连滚带爬地退出去,后背重重撞在腐烂的门框上,
灰尘簌簌落下。我不能待在这。我要离开。立刻。马上。这个念头像救命稻草一样攥紧了我。
可腿是软的,几乎撑不住身体。我几乎是爬出老宅的,院外的天光灰蒙蒙的,
像是隔着一层脏污的毛玻璃。村里依旧死寂,我踉跄着往村口跑,只想离那宅子越远越好。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福伯居然还在。他蹲在那里,像一尊风干的石像,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地面。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慢慢抬起头。他的脸是一种死灰。
看到我逃命的惨状,他咧了咧嘴,那表情比哭还难看。“看到了?”他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喘着粗气,说不出话,只是死死盯着他。“报应……”他低下头,
用几乎听不见的气音喃喃,“都是报应……躲不掉的……谁也躲不掉……”“那是什么?!
”我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声音,嘶哑得自己都陌生,“那些……那些尸体!我的名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福伯浑身一颤,猛地抱住头,
缩成一团:“不能说……说了……都会死……死得更惨……”“告诉我!
”我扑上去抓住他干瘦的肩膀,剧烈地摇晃,“告诉我!!”他猛地抬起头,眼球暴突,
血红的恐惧几乎溢出来:“是债!是你们家欠下的债!三代!整整三代!
她们……她们都是……”他的话卡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撕心裂肺,
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最后,他喘着粗气,眼神涣散地看着我身后老宅的方向,
:“……她在等你……一直等着……拜堂……吉时到了……都得……都得还……”说完这句,
他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精气神,彻底瘫软下去,无论我再怎么问,怎么吼,
他都只是蜷缩着,嘟囔着谁也听不清的呓语。绝望像冰水一样浇下来。我松开他,
一步步后退。村子是问不出任何东西了。他们怕,怕得要死,怕那个所谓的“祖宗”,
怕地底下的东西,怕我,或者怕我背后的什么。我掏出手机,没有信号。唯一的希望,
是镇上的派出所。对,报警。必须报警。地底下有九条人命!这是谋杀!这个念头支撑着我,
几乎是跑着穿过来时那条荒路,跑到镇子上。镇派出所很小,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民警,
听我语无伦次、浑身发抖地说完地窖里的尸体、木牌,他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惊愕,
最后染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他让我等着,进去了好一会儿,
才跟着一个年纪大些、脸色凝重的老民警出来。老民警又仔细问了一遍,
特别是关于木牌上的名字和八字,以及村民的反应。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红溪村……老宅……”他沉吟着,和年轻民警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眼神复杂得让我心沉到底。“你先别急,这事……我们知道了。你先回去等着,
我们立刻上报,安排人手过去勘查。”“我不能回去!”我脱口而出,声音尖利。
“那你在镇上找个招待所先住下,”老民警语气不容置疑,“记住,晚上锁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