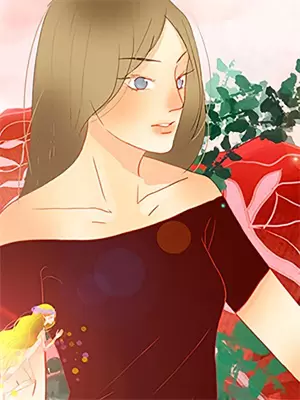......我叫陈俊男,我说谎了.......蹲在便利店门口啃第三根烤肠时,
那辆黑色帕萨特就停在对面路灯底下。车玻璃贴了最深色的膜,像块浸了墨的冰,
把七月的热风都冻得打哆嗦。“俊男,账结一下。”老板娘用指甲敲了敲收银台,
她那枚假钻戒在日光灯下晃得人眼晕,“再赊账,你那件破洞T恤都得押这儿。
”我把最后一截烤肠签子扔进垃圾桶,铁皮桶发出“叮”的轻响,
惊飞了脚边两只偷食的麻雀。“急什么,”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抖出根烟,
打火机“咔哒”响了三下才窜出火苗,“等小爷我把那笔‘零花钱’拿到手,别说烤肠,
你这店我都给你盘下来——改成成人用品店,保准比卖关东煮挣钱。”老板娘翻了个白眼,
转身去擦货架。我叼着烟往帕萨特走,鞋底碾过路边的碎玻璃,咯吱响。拉开车门时,
一股混合着皮革和消毒水的味道涌出来,比我出租屋里的霉味好闻点,但也有限。
后排坐了个穿白衬衫的男人,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手腕上有块青色胎记,
像片没长开的叶子。他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手指关节泛白,
一看就是第一次干这种见不得光的事。“陈先生,”他声音发紧,像被砂纸磨过的钢管,
“东西……带来了吗?”我从裤兜里摸出个用密封袋裹着的U盘,抛了抛,
金属壳在昏暗的车里闪了下光。“周老板倒是会选人,”我靠在副驾座椅背上,吐了个烟圈,
看着烟雾在他头顶散开,“找个连撒谎都不会的来交易,就不怕我黑吃黑?”他喉结动了动,
把信封推过来:“这里是五万,事成之后……”“事成之后?”我打断他,
指尖夹着的烟快烧到过滤嘴,烫得指尖发麻,“周老板没告诉你,我陈俊男办事,
从不信‘之后’?”他脸色瞬间白了,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座椅上。我拿起信封掂量了下,
厚度还行,够我换个新手机——上次跟人抢地盘,手机被踩成了马赛克。“U盘里的东西,
”我把烟蒂弹出窗外,看着它在空中划了个红弧,落在路边的垃圾堆里,
“是你家公子在酒吧跟人飙药的视频,对吧?拍得挺清楚,
尤其是他把那玩意儿往妞儿嘴里塞的时候。”他没说话,肩膀抖得像筛糠。我忽然觉得好笑,
这世道真有意思,有权有势的人,软肋往往比谁都软。“放心,”我把U盘扔给他,
金属壳撞在真皮座椅上,发出清脆的响,“我这人讲究,收了钱,就不做绝事。
”他慌忙把U盘塞进衬衫口袋,手忙脚乱地拉开车门,差点被门槛绊倒。
我看着他踉跄着钻进旁边的小巷,背影跟被狗追的兔子似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发动汽车时,
副驾脚垫上落了根他的头发,黑得发亮。我没在意,一脚油门踩下去,
帕萨特像头昏昏欲睡的老狗,慢吞吞地汇入车流。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根头发会像根针,
迟早要刺破我这看似浑浑噩噩的日子。更不知道,那只被我随手弹出窗外的烟蒂,
会在三天后,烧穿另一件更干净的白衬衫。我把帕萨特停在老城区的拆迁楼底下,
车身上的泥点子跟地图似的,糊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李三儿蹲在楼门口的石墩上,
见我下来,赶紧把烟掐了,手指在裤腿上蹭了蹭。“南哥,”他声音里带着讨好,
比上次跟我借两百块钱时还乖,“那娘们儿就在三楼,刚进去没十分钟。
”我踢了踢他的鞋跟,那鞋后跟都磨歪了,露出里面的硬纸板。“钱带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新旧掺着,
边角卷得像波浪。“一共八千,我跟弟兄们凑了三天才凑齐……”“少废话。
”我把钱夺过来塞进外套内袋,布料摩擦着昨天刚结疤的伤口,有点痒。
“人我帮你‘请’出来,后续的事,别再找我。”李三儿点头跟捣蒜似的:“明白明白,
南哥办事,我们放心。”我没理他,往楼道里走。楼梯扶手积的灰能埋住脚脖子,每走一步,
就扬起一阵灰,呛得人直咳嗽。三楼拐角处堆着个破沙发,弹簧从烂掉的布里戳出来,
像只瘦骨嶙峋的手。302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女人哼歌的声音,调子挺浪,
是最近流行的那首《午夜探戈》。我推开门时,那女人正对着镜子涂口红,大红色,
涂得嘴唇跟刚吸过血似的。她吓了一跳,口红在嘴角划出道红印,像道血痕。“你谁啊?
滚出去!”我靠在门框上,摸出烟盒,发现空了,随手扔在地上。“李三儿让我来的。
”她脸色变了,手忙脚乱地想去抓桌上的手机。我没动,就看着她,她那点小动作,
在我眼里跟慢镜头似的。果然,她手指刚碰到手机,就又缩了回去,
大概是想起李三儿手里握着她偷卖公司账目的证据。“我没钱。”她声音软了下来,
眼睛瞟着我,眼神里那点算计藏都藏不住,“要不……你放我一马,
我陪你……”我打断她:“少来这套。跟我走一趟,把李三儿的钱还了,这事就算了。
”她咬着嘴唇,红指甲掐进掌心,挤出几个月牙印。“我真没钱,
那笔钱被我男人赌输了……”“那是你的事。”我转身往外走,“给你三分钟,要么自己走,
要么我拖你走。”我在楼梯口等着,听见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接着是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噔噔声。她走出来时,头发乱了,口红晕在下巴上,
倒比刚才那副精心打扮的样子顺眼点。“算你狠。”她瞪我一眼,眼神里有恨,更多的是怂。
我没说话,带着她往楼下走。李三儿早在车里等着了,见我们下来,赶紧拉开车门。
我没上车,靠在车身上,看着李三儿把那女人推上车,引擎发动的瞬间,
我忽然瞥见那女人的手伸出车窗,红指甲在夕阳下闪了下光,像只垂死挣扎的蝴蝶。“南哥,
这是给你的辛苦费。”李三儿从车窗里递出个信封,比刚才给我的油纸包薄多了。
我没接:“不用,记得欠我的那顿酒就行。”李三儿愣了下,随即点头哈腰地应着。
车开走时,我看见后视镜里那抹红色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子拐角。
那天晚上我去了常去的网吧,开了台机器打游戏,打到后半夜,眼皮越来越沉。
趴在键盘上快睡着时,忽然梦见那只红指甲,死死掐着我的手腕,掐出一圈血印,
跟我小时候被我爸用皮带抽出来的印子差不多。我猛地惊醒,键盘上的烟灰掉了一身。
摸出手机看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屏幕亮着,映出我眼下的黑眼圈,像两只没睡醒的熊猫。
.......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下得不大,却黏糊糊的,把空气里的灰尘都泡成了泥。
我被冻醒时,发现自己还在网吧沙发上躺着,身上盖着件不知是谁丢的外套,
一股子汗味混着烟味。走出网吧,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街对面的早餐摊冒着白气,
油条在油锅里炸得滋滋响,香气顺着风飘过来,勾得我肚子直叫。刚要过马路,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里面传来个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被猫抓过的毛线。
“陈……陈先生吗?求你救救我……”我皱了皱眉:“哪位?
”“我是……我是昨天那个……李三儿把我关起来了,
他说不还钱就……就把我送进派出所……”我想起来了,是那个红指甲女人。“关哪儿了?
”“在……在郊区的废弃工厂,他说你认识路……”我挂了电话,站在雨里骂了句脏话。
这李三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抓个人还得让我擦屁股。拦了辆出租车,报了地址。
司机是个话痨,一路跟我叨叨最近的新闻,说什么城郊发现具女尸,手脚被捆着,
扔在河里泡了三天,身份证都泡发了,辨不出模样。我没搭话,看着窗外的雨。
雨刷器来回摆动,把玻璃上的雨水扫成一道道水痕,像谁在上面划了无数道口子。
到了废弃工厂门口,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往里开,我付了钱,自己踩着泥往里走。
工厂的铁门锈得掉渣,一推就发出“吱呀”的惨叫,惊得屋檐下的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里面很静,只有雨声敲在铁皮屋顶上的噼啪声。我往里走了没几步,
就看见李三儿蹲在一堆废铁旁边抽烟,见我来了,赶紧站起来,脸上堆着笑,比哭还难看。
“南哥,你咋来了?”“人呢?”我踢了踢脚边的空酒瓶,玻璃渣陷进泥里,
只露出个尖他往旁边指了指,仓库角落的柱子上,红指甲女人被绳子捆着,嘴里塞着块破布,
头发被雨水打湿,黏在脸上,看着跟落汤鸡似的。“南哥,这娘们儿嘴硬,说啥也不还钱,
我才……”“我让你逼她还钱,没让你非法拘禁。”我打断他,走到女人跟前,
把她嘴里的破布扯下来。她刚能说话,就开始哭嚎:“救我!他是个疯子!他昨天打我!
”我看了眼她胳膊上的淤青,青一块紫一块的,跟我小时候被邻居家孩子打的差不多。
“李三儿,”我转身看着他,“把人放了。”“南哥,这……”“小爷让你把人放了。
”我掏出烟,点上,烟雾在雨里散得很快,“钱的事,我来解决。”李三儿咬了咬牙,
从口袋里摸出把小刀,蹲下去割绳子。女人得救了,却不敢动,缩在墙角发抖,
眼神里的恐惧比刚才还重。我扔给她一百块钱:“自己打车回去。”她捡起钱,
跟兔子似的跑了,高跟鞋踩在泥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响,没一会儿就没了影。“南哥,
这钱……”李三儿急了。“小爷我替她还算了。”我把昨天他给我的八千块扔给他,
“不够的,算我的。”李三儿愣住了,手里的钱被雨水打湿,变得沉甸甸的。“南哥,
你这是……”“少废话。”我转身往外走,“以后别再干这种蠢事。”走出工厂时,
雨下大了,砸在身上生疼。我没打车,就沿着马路走,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流进眼睛里,
涩得慌。路过一个垃圾桶时,看见里面扔着个被水泡得发胀的身份证,
照片上的女人笑靥如花,眉眼间有点眼熟,像刚才跑掉的那个红指甲女人。我蹲下去看了看,
名字被水泡得模糊了,只能看清地址,是城郊的一个小区,离发现女尸的河边不远。
我没多想,站起来继续走。雨太大,把什么都冲得乱七八糟,谁还在乎一张泡发的身份证呢?
......我是被阳光晒醒的,眼皮子上像糊了层猪油,黏糊糊的。
出租屋的窗帘烂了个洞,阳光从洞里钻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道亮晃晃的线,
飞尘在里面翻跟头,看得人眼晕。摸出手机看时间,下午两点。屏幕上有三个未接来电,
都是王胖子的。这死胖子,除了催债还能有什么事。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脚踩在地板上,
黏住了——不知道是昨晚带回来的泥,还是上次打翻的泡面汤干了的痕迹。
空气里飘着股馊味,混合着墙角霉斑的气息,比网吧的厕所还上头。刚套上T恤,
门就被砸得咚咚响,跟拆迁队来了似的。“陈俊男!你他妈再不开门,我卸了你门板当柴烧!
”王胖子的大嗓门隔着门板传进来,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我慢悠悠地开了门,
王胖子那张油腻的脸堵在门口,脖子上的金链子比我上个月见时又粗了一圈,
估计是又刮了哪个冤大头的油水。他身后跟着两个小弟,一个染着绿毛,一个纹着花臂,
眼神凶巴巴的,可惜嘴角还沾着薯片渣,看着有点滑稽。“哎呦喂,胖哥,稀客啊。
”我往旁边挪了挪,让他们进来,“要不要喝瓶可乐?过期三天,味儿正。”王胖子没理我,
一屁股坐在我那把快散架的折叠椅上,椅子发出“嘎吱”的呻吟,像在求饶。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他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拍在桌上,“上个月借我的五万,该还了吧?
”那是张借条,我签的名龙飞凤舞,最后一笔还带了个勾,当时觉得特潇洒,
现在看来跟个笑话似的。借条边缘沾着块油渍,不知道是红烧肉还是回锅肉的,
看着有点亲切——毕竟我快半个月没沾过荤腥了。“胖哥,再宽限几天呗。
”我摸出烟递给他,他没接,自己从怀里掏出盒中华,弹出一根叼在嘴里,
绿毛赶紧凑上去点火。“宽限?”王胖子吐了个烟圈,烟圈飘到我面前炸开,
“你上次说等你妈寄钱,结果你妈电话打不通;上上次说等你把游戏机卖了,
结果游戏机早被你当给北边的傻子了。陈俊男,你当我王胖子是傻子?”我挠了挠头,
嘿嘿笑:“这次不一样,小爷我昨天刚赚了笔外快,就是……不小心掉下水道了。
”花臂“嗤”地笑了一声,王胖子瞪了他一眼,他立马收了声。“少来这套,
”王胖子站起身,折叠椅终于松了口气,“今天要么还钱,
要么……”他指了指我胳膊上的纹身,“把你这龙给我剜下来当利息。
”我这纹身是去年在夜市摊纹的,五十块钱,龙身歪歪扭扭,跟条泥鳅似的。我摸了摸,
笑道:“胖哥,这玩意儿剜下来也不值钱啊,要不我给你唱首歌?
我唱《征服》特像那谁……”“唱你妈个头!”王胖子一脚踹在桌子上,桌上的空酒瓶倒了,
滚到地上摔碎了,玻璃渣溅到我脚边,差点划破拖鞋。“给你最后半小时,要么凑钱,
要么跟我走趟医院——不是看病,是卸零件。”他带着人摔门而去,门板晃了晃,
掉下块墙皮,正好砸在我脚背上。我没动,蹲下去捡地上的玻璃渣,指尖被划破了,
血珠渗出来,滴在那张沾着油渍的借条上,晕开一小朵红。半小时怎么凑五万?
我翻遍了出租屋,最后在枕头底下摸出二十三块五,还有半包皱巴巴的烟。
窗外的麻雀又开始叫了,叽叽喳喳的,像在嘲笑我。我忽然想起周老板,
就是昨天让我送U盘的那个。他儿子的视频,我其实留了备份。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我就打了个寒颤。跟王胖子耍耍嘴皮子没事,动周老板的主意,那可是在老虎嘴里拔牙。
但看着地上的玻璃渣,还有王胖子那副要吃人的样子,我咬了咬牙。拨通周老板的电话时,
我的手有点抖。电话响了五声才被接起,周老板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迷糊:“谁啊?
”“周老板,是我,陈俊男。”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昨天那事儿,有点小麻烦。
”“什么麻烦?”他的声音瞬间清醒了,带着警惕。“我这儿有个兄弟,急需点钱,
你看……”“你想讹我?”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像结了冰,“陈俊男,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知道,周老板是大人物。”我赔着笑,手心全是汗,“但我这兄弟是混道上的,
要是拿不到钱,说不定会去你公司门口……聊聊你家公子的爱好。”电话那头沉默了,
只有电流的滋滋声。过了大概半分钟,周老板说:“地址。”我报了地址,挂了电话,
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靠在墙上,看着那张借条上的血印,忽然觉得这事儿干得真操蛋。
但转念一想,反正我陈俊男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多一件少一件,又有什么区别?
四十分钟后,有人敲门。我以为是王胖子,开门却看见个穿西装的年轻人,
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周总让我来的。”他把袋子递给我,眼神里满是鄙夷,
像在看条臭水沟里的老鼠。袋子里是五万块现金,用银行的纸带捆着,整整齐齐。
我数都没数,就往王胖子的手机上发消息让他明天来拿。傍晚的时候,
王胖子发了条短信:算你识相。我没回,坐在地上,看着窗外的太阳一点点沉下去。
天空从橘红色变成深紫色,最后黑得像块墨。出租屋里没开灯,我就坐在黑暗里,
摸出那半包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完了,我才发现,那包现金里,夹着张纸条,
是周老板的笔迹,只有四个字:等着瞧。......我是被尿憋醒的,摸黑往厕所跑,
差点被地上的啤酒瓶绊倒。窗外天刚蒙蒙亮,楼下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油锅滋滋响,
混着豆浆的甜香飘上来,勾得我肚子直叫。刚系好裤子,手机就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归属地是邻市。我没多想,接了起来,里面传来个老太太的声音,
颤巍巍的:“请问……是俊男吗?”我愣了下,这声音有点耳熟。“您是?
”“我是你张奶奶啊,住在你家隔壁的那个……”张奶奶?我想起来了,
是我小时候住的老家属院的邻居,头发白得像棉花糖,总爱给我塞水果糖。
我上初中那年搬了家,就再也没见过她。“张奶奶?您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是你妈告诉我的,”老太太叹了口气,“俊男啊,你妈她……住院了。
”我手里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屏幕没碎,但电池摔出来了。
我手忙脚乱地把电池装回去,开机,再打过去,手还在抖。“我妈怎么了?”“脑溢血,
昨天半夜送进医院的,现在还在抢救……医生说,要不少钱呢。”张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妈不让告诉你,怕你担心,可我寻思着,你是她唯一的儿子啊……”后面的话我没听清,
脑子里嗡嗡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我妈,
那个总爱骂我没出息、却偷偷在我书包里塞钱的女人,
那个说再也不管我、却在我被人打的时候拿着扫帚冲上去的女人……“医院在哪儿?
”我吼了出来,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张奶奶报了个地址,是邻市的中心医院。我挂了电话,
没换衣服,穿着睡衣就往外跑,楼道里的声控灯被我跺得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拦了辆出租车,报了地址,司机看我穿着拖鞋睡衣,眼神怪怪的。“师傅,快点,越快越好,
钱不是问题。”我摸出周老板给的剩下的钱,抽了几张塞给他。司机没废话,
一脚油门踩到底,出租车像箭似的窜了出去。窗外的树往后退,快得成了绿影子,
我却觉得太慢,慢得让人发疯。我妈住院要花钱,我哪来的钱?
周老板的五万块全给了王胖子,我身上就剩几百块。刚才从出租屋跑出来太急,
连钱包都没带。我摸出手机,翻通讯录,翻了半天,发现能借钱的人,一个都没有。
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要么早就被我借怕了,要么根本就是酒桌上的虚情假意。
车过收费站时,我看见了个广告牌,上面是家琴行的广告,写着“高价回收二手乐器”。
我忽然想起,我爸生前有把吉他,放在老家属院的储藏室里,那是他年轻时买的,
宝贝得跟什么似的,说那是他的“青春”。我让司机绕到老家属院,家属院早就破败了,
墙皮掉了一半,门口的石狮子缺了只耳朵。张奶奶在门口等着,见我来了,
拉着我的手就哭:“俊男啊,你可来了,你妈她……”“张奶奶,我先去拿点东西,
马上就去医院。”我挣开她的手,往储藏室跑。储藏室的锁锈死了,我找了块砖头砸了半天,
才把锁砸开。里面一股霉味,蜘蛛网结得跟窗帘似的。吉他靠在墙角,琴盒上全是灰,
我吹了吹,打开琴盒,吉他的弦断了一根,琴身上落着片干枯的叶子,
不知道是哪年飘进来的。我抱起吉他,琴身有点沉,比我记忆里重多了。
小时候我总趁我爸不在家,偷偷拿出来弹,弹得不成调,每次都被他追着打。他打我的时候,
我妈就护着我,骂我爸:“孩子玩玩怎么了?你那破吉他比儿子还重要?
”我把吉他塞进琴盒,抱着往琴行跑。琴行老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了看吉他,
又看了看我,皱着眉说:“这琴太旧了,弦也断了,最多给你五百。”“五百?”我急了,
“这是红棉牌的,当年可贵了!”“现在没人要这种老古董了。”老板低头玩手机,
“要不要?不要我可关门了。”我看着吉他,琴身上有块小小的磕碰,
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摔的,我爸心疼了好几天。我咬了咬牙:“卖!”拿着五百块钱冲出琴行,
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到了抢救室门口,张奶奶迎过来说:“医生刚才出来了,
说情况不太好,让准备钱……”我把五百块钱塞给张奶奶,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喘不上气。“张奶奶,您先拿着,我再去想办法。”我转身往外跑,跑到医院门口,
看见个乞讨的老头,面前放着个破碗,里面有几块零钱。我忽然觉得,我跟他也没什么区别,
都是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可怜虫。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里面传来周老板的声音,冷冰冰的:“陈俊男,玩得开心吗?”我心里咯噔一下,
知道他要报复了。“周老板,我……”“你妈在中心医院抢救室,对吧?”他笑了,
笑声像蛇吐信子,“我刚给院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好好照顾’一下。”我的血瞬间冻住了,
握着手机的手抖得厉害:“周建军,你他妈不是人!”“我是不是人,你很快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