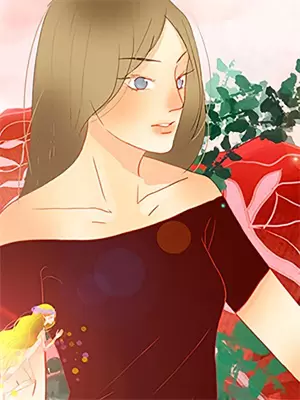1 毒蛇缠腰冰冷黏腻的触感,像一条蛰伏的毒蛇,猝不及防地贴上我的后腰,
硬生生钻透薄薄的棉质家居服,激得我脊椎骨缝里都渗出寒气。不是错觉,那锐利的尖端,
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精准地顶在某个能瞬间让人丧失行动力的位置。“别动,林柚。
”声音自身后极近的地方传来,气息滚烫,拂过我颈后的碎发,激起一阵细微的痒意,
却又被那话语里淬了冰的寒意冻得粉碎。我认得这声音。顾泽,
住在走廊尽头那个新搬来、过分安静的邻居。此刻,这声音像一条冰冷的蛇,
缠绕上我的听觉神经。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本能地屏住。
视线却固执地、带着点不合时宜的恍惚,向上飘去。越过他线条紧绷的下颌,
落在他垂落的眼睫上。一滴暗红,浓稠得化不开的血珠,正悬在他浓密的睫毛尖端。
窗外惨白的闪电骤然撕裂墨黑的夜幕,将这滴血映照得惊心动魄,仿佛一枚妖异的红宝石,
摇摇欲坠。它悬在那里,仿佛凝固了时间,带着一种诡异而惊心的美。
雨水疯狂抽打着便利店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发出连绵不绝的、令人心慌的“噼啪”声,
织成一张嘈杂而压抑的网。白炽灯管发出低低的嗡鸣,光线惨白而冰冷,
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照亮了脚下这片小小的、混乱的修罗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浓烈的血腥气,如同生锈的铁屑,
霸道地冲撞着鼻腔。
它混合着顾泽身上传来的、一种近乎诡异的干净松木冷香——我曾在他晾晒的衣物上闻到过。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气息在此刻狭小的空间里野蛮地纠缠、厮杀,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反差。
更深处,似乎还潜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腻腐烂气息,不知从哪个角落幽幽渗出,
无声地侵蚀着人的意志。我僵硬的视线终于艰难地从那滴血珠上移开,缓缓向下扫视。
目光所及,心脏猛地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他的深色卫衣下摆,湿透了。
深色的布料被浸染成更深的、近乎墨黑的一块,紧紧贴在他身上。
那绝不是雨水能造成的效果。暗红的液体正顺着衣料纤维的纹理,一滴,一滴,
沉重而缓慢地砸落在脚下廉洁光滑的瓷砖地上。
它们汇聚成一小滩粘稠的、反着光的暗色镜面,
边缘还在极其缓慢地、如同活物般向四周蠕动、蔓延,无声地勾勒着死亡的形状。
那柄抵住我后腰的美工刀,金属的冰冷质感透过布料,清晰地烙印在我的皮肤上,
像一块无法摆脱的寒冰。每一次微不可察的移动,都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深入骨髓的寒意,
提醒着我此刻处境的极端危险。“跟我走,”顾泽的声音贴得更近了,
几乎是含住了我的耳垂,那滚烫的气息却只让我感到彻骨的冰冷,“或者死在这。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针,扎进我的耳膜。我的大脑一片混沌,像塞满了湿透的棉花。
恐惧本该是此刻唯一的旋律,它确实存在,在四肢百骸里尖叫。
但另一种更顽固、更不合时宜的东西,
却像礁石般顽固地浮了上来——一种近乎麻木的迟钝感,
一种长年累月形成的、面对巨大冲击时的自我保护性隔离。眼前的景象光怪陆离地扭曲着。
那滴悬在他睫毛上的血珠,在惨白灯光下折射出妖异的光。脚下那摊粘稠蔓延的暗红,
像一张正在无声狞笑的嘴。他身上那股松木冷香与血腥的混合气味,
无孔不入地钻进我的肺腑……所有的感官刺激都尖锐到了极致,
却又被一层无形的、厚厚的膜隔绝在外,隔着一层毛玻璃,显得模糊而失真。
我的思维像生锈的齿轮,艰难地、卡顿地转动着。他……受伤了?很重的伤?
是那个……那个最近闹得人心惶惶的“雨夜割喉魔”干的?
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新闻片段、同事们压低的惊恐议论,像破碎的玻璃渣,
在我混乱的脑海里闪现。那个专挑独行女性下手、手段残忍的疯子……顾泽是遇到了他?
然后逃出来了?这个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突兀地在我一片荒芜的恐惧沼泽里冒了出来。
逻辑支离破碎,却带着一种溺水者抓住浮木般的本能。他需要帮助。
他浑身是血地出现在这里,用刀威胁我……也许只是为了求救?人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下,
行为是会失控的……对,一定是这样。他是我邻居,虽然沉默寡言,
但看起来……看起来并不像坏人。那点可怜的、源自日常点头之交的浅薄印象,
此刻成了我摇摇欲坠的心理支点。抵在后腰的刀尖又往前顶了顶,刺痛感尖锐地传来,
彻底压垮了我本就脆弱的右臂。“……好。”喉咙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顾泽紧绷的身体似乎几不可察地放松了一丝丝,
但那把刀的位置没有丝毫移动。“别耍花样。”他低低警告,声音沙哑得像砂砾摩擦。
他一只手依旧牢牢控制着我,
另一只手粗暴地拽过收银台旁我那个印着便利店Logo的帆布包,
胡乱塞了几包货架上的压缩饼干和瓶装水进去,动作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
我像个被抽掉提线的木偶,被他半推半搡着,踉跄地走向便利店的后门。
沉重的金属门被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嘎”声,
潮湿冰冷的夜风裹挟着更大的雨点猛地灌进来,吹得我一个激灵。
就在被推出门、彻底融入外面狂暴雨夜的瞬间,
银台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勾住——那是我今天刚换上的、一个塑料招财猫造型的零钱盒。
猫爪的位置,本该稳稳放着一张二十元纸币,作为找零的备用金。现在,那里空空如也。
我愣了一下。那二十块钱呢?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交班时还在……这个微不足道的疑惑,
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只激起一圈微澜,
瞬间就被身后巨大的、裹挟着血腥与松木冷香的压迫感吞没。
顾泽的手像铁钳般箍着我的胳膊,将我狠狠拉入门外倾盆的暴雨和未知的黑暗之中。
便利店后门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在身后彻底断绝,如同斩断了我与安全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
狂暴的雨点瞬间劈头盖脸砸下,冰冷刺骨,瞬间浇透了我的头发和单薄的家居服。
顾泽的手像一道冰冷的铁箍,死死钳着我的上臂,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
不容我有丝毫迟疑或反抗。2 暗巷囚笼他拖着我,以一种近乎粗暴的速度,
一头扎进公寓楼侧面那条狭窄、堆满杂物的昏暗小巷。黑暗如同粘稠的墨汁,兜头泼下,
瞬间吞噬了仅存的光线。眼睛在骤然的明暗转换中完全失效,只剩下耳边震耳欲聋的雨声,
冲刷着墙壁,敲打着废弃的铁皮桶,汇成一片混沌而充满压迫感的轰鸣。脚下坑洼不平,
污水四溅,每一次踩下去都带起粘腻的泥泞和未知的触感,冰冷湿滑,好几次我差点被绊倒,
全靠他那只冰冷而有力的手死死拽住,才没有一头栽进污秽里。
不知道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穿行了多久,只知道肺里的空气被冰冷的雨水挤压得所剩无几,
他才猛地推开一扇锈蚀得几乎看不出原色的铁门。
一股混合着浓重尘埃、霉菌和陈旧木头气息的浊气扑面而来。他用力将我推了进去。“砰!
”身后的铁门被狠狠关上,隔绝了外面喧嚣的雨幕,
也隔绝了最后一丝来自外界的光线和声响。世界骤然陷入一种诡异的、令人心慌的绝对死寂。
黑暗中,传来他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像一头受伤的困兽。接着是窸窸窣窣摸索的声音,
片刻后,“啪嗒”一声轻响,
一盏悬挂在低矮天花板上的、蒙着厚厚灰尘的白炽灯泡亮了起来。
昏黄、暗淡的光线如同垂死之人的叹息,勉强驱散了近身的黑暗,
却将更远处的阴影拉扯得更加扭曲、深重。我这才看清自己身处何地。这是一间地下室。
空间狭小、低矮,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墙壁是裸露的、布满霉斑和剥落痕迹的水泥,
地面同样冰冷粗糙。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光秃秃的铁架床,
上面胡乱堆着一床颜色灰暗、辨不出原色的薄被。
角落里散落着几个空罐头盒和一些速食包装袋,
里弥漫着灰尘、霉菌、食物残渣腐败的微酸以及……那股始终萦绕不去的、淡淡的松木冷香。
这香气在此刻浑浊的空气里,显得格外突兀和冰冷。顾泽背对着我,
站在唯一一张破旧的木桌旁。他脱掉了那件被血浸透的深色卫衣,随手扔在满是污渍的地上。
裸露的上半身,在昏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缺乏血色的冷白,肌肉线条流畅却紧绷,
像一张拉满的弓。然而,那冷白的皮肤上,赫然分布着几道新鲜的、皮肉翻卷的伤口,
暗红的血痂触目惊心,其中一道斜斜划过肩胛骨,狰狞得如同一条丑陋的蜈蚣。
我的呼吸猛地一滞。不是因为伤口本身,而是……那伤口周围的皮肤,光滑完好,
没有一丝淤青或搏斗留下的痕迹。那不像激烈反抗留下的,
反而……更像是某种冷酷而精准的切割?这个念头如同毒蛇,猛地噬咬了我一口。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缓缓转过身。脸上残留的水痕混着几缕湿透的黑发,
紧贴着他过分苍白的脸颊。那双眼睛,在昏黄的光线下,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幽暗,
沉寂,所有的情绪都被牢牢锁死在深处,只余下令人心悸的空洞。他一步步走近,脚步无声,
踩在水泥地上,却像踏在我的心尖上。冰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停在我面前,
距离近得能感受到他身体散发出的、混杂着血腥气的寒意。他抬起手,
那只骨节分明、沾着些许暗红污迹的手,缓缓伸向我的脸颊。我浑身僵硬,
血液似乎都冻结了,连闭眼躲避的力气都没有。指尖带着刺骨的冰凉,
轻轻拂过我的眼角下方,拭去一滴不知何时滚落的、同样冰冷的泪水。那触感,
像一块刚从停尸房取出的金属贴上了皮肤。“哭?”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玩味的腔调,在死寂的地下室里清晰地回荡,每一个音节都像冰锥,
凿在紧绷的神经上,“现在才害怕?”他微微歪了下头,动作带着一种非人的僵硬感,
目光像探照灯,一寸寸扫过我惨白的脸,似乎在仔细研究一件新奇的、刚刚到手的藏品。
“晚了。”他轻轻吐出最后两个字,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
更像某种冰冷器械的牵拉,透着一股子非人的诡异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满足感。那晚之后,
时间在这间水泥坟墓里失去了刻度。铁门紧闭,只有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不分昼夜地亮着,
像一只永不瞑目的眼睛。顾泽成了这方寸之地的绝对主宰,
一个阴晴不定、散发着致命寒意的看守。他把我锁在这里。是真的锁。一条沉重的铁链,
一端焊死在墙角粗大的水管上,另一端,扣在我的左脚踝上。冰冷的金属贴着皮肤,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的处境。
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铁链长度所及——一张冰冷的铁架床,一个散发着霉味的破旧马桶,
仅此而已。饥饿是常态。食物和水是他唯一的食舍。
3 深夜鬼影有时他会扔进来一袋干硬的面包和一瓶冰冷的矿泉水,有时则长时间消失,
留我在昏沉与胃部的绞痛中煎熬。他的出现毫无规律,像幽灵,
开门关门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只有那骤然侵入的寒意和松木冷香宣告着他的到来。有时,
他会长时间地坐在那张唯一的破木椅上,背对着我,沉默得如同一尊冰冷的石雕。
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他僵硬的背影,空气凝固得能拧出水来,
只有我手腕上铁链偶尔碰撞发出的轻微“叮当”声,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死寂。
每一次声响都让我心惊肉跳,生怕惊扰了这尊沉默的凶神。但更多的时候,
是无声的、令人头皮发麻的注视。他就站在几步之外,靠在冰冷的水泥墙上,双臂环抱,
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像两潭凝固的墨,毫无波澜地、长久地锁定在我身上。目光如有实质,
冰冷、粘稠,带着一种令人极度不适的审视感,仿佛在观察一只困在玻璃缸里的昆虫,
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摆弄。我被那目光钉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吞咽冰渣。最让我灵魂都为之冻结的,是深夜。
当我蜷缩在铁架床上那床薄得几乎不存在的、散发着陈腐气味的被子里,
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陷入半梦半醒的混沌时,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知觉会悄然降临。
锁链会极其轻微地震动一下,发出几乎听不见的金属摩擦声。紧接着,
一股冰冷的、带着松木气息的阴影笼罩下来。顾泽无声无息地站在床边。
我能感觉到他俯下身,动作轻缓得如同鬼魅。然后,一双冰冷的手,
指尖的温度低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会轻轻拂过我的脸颊,
或者极其仔细地、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专注,将被角一点点、一点点地掖紧。那触感,
冰冷、滑腻,像某种冷血爬行动物的腹部蹭过皮肤。每一次触碰,都激起我全身汗毛倒竖,
血液瞬间冻结。我死死闭着眼睛,连睫毛都不敢颤动一下,全身的肌肉绷紧得像石头,
用尽全部意志力伪装沉睡。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巨大的恐惧几乎要冲破喉咙。
他是在确认猎物是否安分?还是……在享受这种掌控?每一次掖好被角,他并不会立刻离开。
那冰冷的、充满压迫感的阴影会停留很久,久到我几乎要在这种无声的酷刑中窒息。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投注在我脸上的目光,
带着一种令人骨髓发寒的专注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扭曲的满足感。时间被拉得无限漫长,
每一秒都是煎熬。直到他终于无声地直起身,那股冰冷的阴影缓缓退去,
锁链再次发出极轻微的声响,我才敢在黑暗中,
极其缓慢地、贪婪地吸入一口带着霉味的冰冷空气,如同濒死的鱼。日复一日。
铁链、沉默、冰冷的注视、深夜鬼魅般的掖被角……这间水泥囚笼,成了我全部的世界。
恐惧如同藤蔓,早已深深勒进骨缝,最初的惊骇渐渐沉淀为一种沉重的、近乎麻木的绝望。
顾泽是疯子,是恶魔,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究竟为何囚禁我?
那个“雨夜割喉魔”……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个便利店消失的二十块钱……纷乱的疑问在死寂中盘旋,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时间在这里腐烂,连同我残存的希望。4 血色真相直到那天下午。顾泽又消失了很久。
饥饿感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胃壁,喉咙干得发痛。地下室浑浊的空气沉闷得让人昏昏欲睡。
我蜷缩在冰冷的铁架床边,背靠着粗糙的水泥墙,
意识地扫过室内唯一能看到的、属于他的私密空间——墙角那个敞着门的、破旧不堪的衣柜。
里面胡乱塞着几件他换下来的深色衣物,还有一个瘪瘪的登山包。
我的视线漫无目的地逡巡着,掠过那些熟悉的、散发着松木冷香的布料……突然,
我的目光死死钉住了。在衣柜最底层,一堆揉皱的深灰色T恤下面,露出了一小截金属表带。
那绝不是顾泽的东西。那表带的颜色、款式……带着一种奇异的熟悉感。
心脏毫无征兆地开始狂跳,像一面被重锤擂响的破鼓,咚咚咚地撞击着肋骨,
震得我耳膜发疼。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头皮阵阵发麻。
铁链的长度刚好能让我勉强够到衣柜的边缘。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了过去,
动作因为恐惧和铁链的束缚而显得笨拙又急切。冰冷的铁环摩擦着脚踝,带来一阵刺痛,
但我完全顾不上了。颤抖的手伸进那堆散发着松木气息的T恤里,不顾一切地往下扒拉。
终于,指尖触到了那冰冷的金属。我猛地将它拽了出来。整个世界仿佛瞬间失声。
昏黄的白炽灯光下,我掌中静静躺着一块女式腕表。小巧的银色表盘,
边缘镶嵌着一圈细细的碎钻,在灯光下反射出微弱却刺眼的光芒。粉色的皮质表带,
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沾染着几处早已干涸、变成深褐色的……污渍。嗡——大脑一片空白,
随即是尖锐的耳鸣。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这是苏晓的表。
是我最好的闺蜜苏晓,生日时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块!她爱若珍宝,几乎从不离身!那圈碎钻,
那粉色的表带……我绝不会认错!苏晓……苏晓已经失踪**个月了。
就在那个同样下着暴雨的深夜,就在离我们公寓楼不远的那条偏僻小巷……后来,
警察找到了她的背包,里面一片狼藉,唯独少了这块表。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是被凶手拿走了……当作……战利品?
而现在……它竟然藏在顾泽的衣柜里!藏在这些散发着松木冷香的衣服下面!
那些深褐色的污渍……是什么?!“好看吗?”一个冰冷的声音,
毫无预兆地、像毒蛇一样贴着我的后颈响起。我魂飞魄散,猛地回头。
顾泽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如同鬼魅。
铁门甚至没有发出过一丝声响。他高大的身影挡住了门口微弱的光线,
投下一片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其中。他逆着光,脸上的表情模糊不清,
只有那双眼睛,在昏暗中亮得惊人,像两点燃烧的鬼火,牢牢锁定在我脸上,
锁定在我手中那块沾血的表上。极致的恐惧如同海啸,瞬间将我吞没。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撞击,几乎要破膛而出。身体里的血液仿佛瞬间被抽干,
四肢冰冷僵硬得如同石膏。巨大的惊恐扼住了我的喉咙,连一声尖叫都发不出来。
眼泪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滚烫的液体瞬间模糊了视线,顺着冰冷的脸颊疯狂滑落。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囚禁我、深夜为我掖被角的“邻居”,
看着这个衣柜里藏着苏晓遗物的恶魔,巨大的绝望和悲愤像毒藤一样缠绕住心脏,
勒得我无法呼吸。喉咙里终于挤出一声破碎的呜咽。顾泽向前跨了一步,彻底走出了阴影。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他的嘴角,竟然噙着一丝冰冷的、近乎愉悦的笑意。那笑容扭曲,
毫无温度,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满足感。他微微俯身,
那张过分俊美却苍白如纸的脸凑近我泪流满面的脸。冰冷的指尖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温柔,
轻轻拂开我黏在额角的湿发。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瞬间灵魂出窍的动作。他低下头,
冰凉的、毫无血色的唇,轻轻贴上我沾满泪水的脸颊。
舌尖带着一种滑腻的、令人寒毛直竖的触感,缓慢地、极其清晰地,
舔舐掉我脸上滚烫的泪水。那感觉,像一条冰冷的毒蛇滑过皮肤。“现在才害怕?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叹息的腔调,气息喷在我的耳廓,
激起一片细小的鸡皮疙瘩。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针,扎进我的神经。他稍稍退开一点,
那双深不见底的、燃烧着诡异火焰的眼睛,
近距离地、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被恐惧彻底击溃的脸庞,嘴角那抹冰冷的笑意加深了,
带着一种残忍的、欣赏猎物绝望的满足感。他轻轻吐出最后两个字,像冰冷的判决:“晚了。
”“晚了”两个字,像两枚烧红的铁钉,狠狠楔进我的耳膜,烫得我灵魂都在战栗。
顾泽眼中那种欣赏猎物垂死挣扎的冰冷快意,像毒液注入血管,瞬间冻结了我奔涌的泪水。
极致的恐惧反而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催生出一股诡异的、近乎虚无的麻木。我瘫坐在地上,
背靠着冰冷的铁架床腿,手中那块沾着苏晓血迹的腕表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痛着掌心。
顾泽没有立刻动作。他居高临下地站着,阴影如同沉重的棺盖压在我身上。
他似乎在享受这死寂中弥漫的绝望,嘴角那抹残忍的笑意未曾消散。时间凝固了,
只有地下室浑浊的空气在昏黄的灯光下缓慢流淌,带着尘埃和血腥气的味道。
5 致命反击就在这时——一阵极其细微、却异常刺耳的电流杂音突兀地响起,
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死寂。声音来自墙角那张破木桌。桌面上,
一个蒙着厚厚灰尘、早已被我们遗忘的老旧收音机,顶部的电源指示灯,
突然闪烁起一点微弱、诡异的红光。它像垂死之人的眼睛,挣扎着亮起。我和顾泽的目光,
几乎同时被这异动吸引过去。那点红光闪烁了几下,仿佛在积蓄最后的力量。紧接着,
一阵更加刺耳、扭曲的调频噪音猛地爆发出来,尖锐得如同指甲刮过玻璃,
瞬间充斥了整个狭小的空间,刺得人耳膜生疼。噪音持续了令人心悸的几秒钟,然后,
一个被严重干扰、断断续续、却异常清晰冷静的男性播音员声音,顽强地穿透了电波的扭曲,
月的‘雨夜割喉魔’连环伤人案……重大突破……”顾泽脸上那种掌控一切的、冰冷的笑意,
瞬间凝固了。像一张骤然碎裂的面具。他微微侧过头,
目光死死钉在那台闪烁的破旧收音机上,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这个角落里的死物。
一股难以言喻的、极其细微的僵硬感,爬上了他挺直的脊背。收音机里的声音在干扰中断续,
深表歉意……”“模仿作案……王某某……供认不讳……顾某……排除嫌疑……”每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