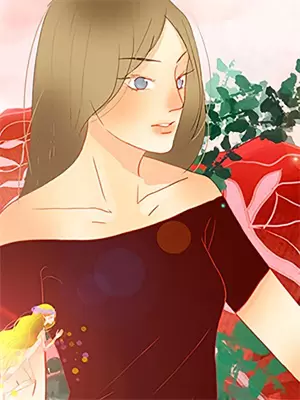>全球人类手背浮现死亡倒计时。>我妻子林晚的倒计时是1年,她的初恋陈默只剩1天。
>她跪在玻璃渣上,用婚姻绑定协议逼我转移十年生命。>“他救过我命!十年换你六十年,
不过分吧?”>我笑着签字,她不知道绑定协议有个隐藏条款。>当陈默获得时间后,
我救她的真实记忆也同步转移。>他欣喜若狂:“当年救你的英雄是我才对!
”>林晚突然浑身冰冷——她再无法感受我的爱意。>她发疯般求我收回时间,
却亲眼看着陈默倒毙街头。>倒计时归零时,她在我面前一寸寸化为飞灰。
---死亡倒计时出现的那天,世界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又猛地被推入最高音量。
天空毫无预兆地暗沉下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源自生命本能的悸动攫住了每一个人。紧接着,
手背皮肤传来一阵短暂而奇异的灼烫。低头看去,深蓝色的数字,
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冰冷权威,清晰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左手手背。
**00:00:00:00:00:00**。这是最初的形态,死神的空白支票。
短暂的死寂后,是山呼海啸般的崩溃。街道上,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对着自己的手背又抓又挠,发出野兽般的嚎叫;花坛边,
穿着校服的女孩瘫坐在地,盯着手背上那串短得令人绝望的数字,无声的眼泪汹涌而出。
汽车喇叭声、尖叫声、歇斯底里的哭喊、疯狂的祈祷……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
煮沸了这座巨大的城市。恐慌如同无形的瘟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瞬间蔓延开,炸裂。
我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二十三楼的高度足以俯瞰脚下这片突然陷入疯狂的蚁穴。
指尖的烟燃着,烟雾袅袅上升,模糊了玻璃上我自己的倒影。我抬起左手,
字上:**60年 00天 08时 23分 17秒… 16秒… 15秒…**六十年。
一个漫长到近乎虚无的承诺。在无数可能只有几小时、几天、几个月的人眼中,
这无疑是神迹。窗外的喧嚣隔着厚重的玻璃,显得沉闷而遥远,像隔着一层水。
我的心跳很稳,一种荒谬的平静笼罩着我。世界末日?或许吧。但此刻,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清晰得如同窗外那轮在诡异天光下显得苍白无力的太阳——林晚。
我的妻子。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抓起桌上的车钥匙,转身冲出办公室,
把身后那片末日景象和同事们或惊恐或呆滞的目光甩在身后。电梯在混乱中慢得像蜗牛,
每一层都有人哭喊着挤进来又挤出去。我干脆推开安全通道的门,沿着楼梯向下狂奔。
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回荡,急促而沉重,每一步都踏在鼓噪的心跳上。
停车场里同样一片狼藉,车辆横七竖八地堵着,喇叭声响成一片。我粗暴地按着喇叭,
强行在混乱的车流中挤出一条路,方向盘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家。
那个我和林晚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地方,此刻像一个脆弱的避风港。钥匙插进锁孔,转动。
门开了一条缝,客厅里压抑的啜泣声就钻了出来,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
我的心猛地一沉,推开门。林晚蜷缩在沙发旁的地毯上,
像一只被暴雨打湿、瑟瑟发抖的雏鸟。她穿着居家的棉质睡裙,长发凌乱地披散着,
遮住了半边脸。露出的那只手死死捂着自己的左手手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那压抑的哭声就是从她指缝里漏出来的,断断续续,撕扯着空气。“晚晚?”我唤她,
声音干涩得厉害。她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那张总是带着温柔笑意的脸,
此刻惨白得像一张揉皱的纸,泪痕交错纵横,眼睛红肿,里面盛满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和茫然。
她看向我,眼神空洞了一瞬,才慢慢聚焦。“沈砚……”她叫我的名字,
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我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想把她揽进怀里。她却像受惊的兔子,
猛地往后一缩,手臂条件反射地藏到身后,仿佛手背上不是倒计时,而是什么丑陋的烙印。
“给我看看。”我尽量放柔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伸手轻轻抓住她的手腕。
她的身体僵硬着,抗拒的力道微弱却固执。最终,还是被我一点点拉开。那只纤细白皙的手,
微微颤抖着。手背上,
判决书:**01年 00天 00时 05分 33秒… 32秒… 31秒…**一年。
只有一年。一股寒气瞬间从脚底窜起,冻结了我的四肢百骸。呼吸变得困难,
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六十年?那又有什么用?
如果她只剩一年……这漫长的岁月对我而言,不过是更加无边无际的荒漠。
我紧紧握住她冰冷的手,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声音哽在喉咙里:“没事的,晚晚,
没事的……会好的……” 这安慰苍白无力得像一层薄纸,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就在这时,
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屏幕在昏暗的光线下固执地亮着。屏幕上跳跃的名字,
像一簇冰冷的火焰,瞬间点燃了我心头的阴霾——**陈默**。林晚像被电击一样,
几乎是扑过去抓起了手机。她的手指因为急切而颤抖,划了好几次才接通。“喂?阿默?
阿默你怎么样?!”她的声音瞬间拔高,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恐和急切,
那是我从未听过的语调,一种超越了恐惧本身的、近乎凄厉的关切。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微弱,
断断续续,带着濒死的喘息,透过听筒隐隐传来,像毒蛇的信子。
“晚晚……我……我的手……只有……一天……不到……” 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绝望。
“一天?!”林晚失声尖叫,整个人剧烈地晃了一下,脸色白得透明,
“怎么会……阿默你别怕!你别怕!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她握着手机,
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目光却下意识地转向我。不,不是转向我,
钉在了我握着她的那只手的手背上——那串刺眼的、漫长的、代表着六十年光阴的蓝色数字。
她的眼神,在那短短一秒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刚才的恐惧、绝望、无助,
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
被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取代——一种在绝境中看到唯一生路的、不顾一切的疯狂,
混杂着难以言喻的愧疚和一种……孤注一掷的狠绝。那眼神像淬了冰的针,
狠狠扎进我的眼底。一个极其不祥的预感,如同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绕住我的心脏,
越收越紧。“沈砚……”她挂断电话,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冷静,冷静得可怕。她挣脱我的手,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仍蹲在地上的我。“帮帮我。”她说,
每一个字都像冰珠砸在地板上,“不,帮帮陈默。”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要鼓起毕生的勇气,
吐出那句注定将我拖入深渊的话:“把你的时间……匀给他一点。”匀一点?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荒谬感排山倒海般袭来。我抬头,
撞进她那双不再有恐惧、只剩下某种偏执决断的眼睛里。“林晚,”我站起身,
声音低沉得吓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她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泪水再次汹涌而出,但眼神却异常凶狠,“他只有一天了!一天!
沈砚!你还有六十年!整整六十年啊!分给他十年……不,哪怕五年!
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可那是他的命啊!”她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指向虚无的空气,
仿佛那个只剩一天的男人就在眼前。“九牛一毛?”我重复着这四个字,
每一个音节都带着冰碴子。心口那个地方,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揉捏,
疼得我几乎直不起腰。六十年是漫长,可凭什么要用我的命,去填她心尖上那个男人的窟窿?
“晚晚,你冷静点。”我试图去拉她的手,想找回那个我熟悉的、温婉的妻子,
“现在全世界都乱了,一定有办法的,也许……”“没有也许了!”她猛地甩开我的手,
力气大得出奇,指甲在我手背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红痕。她踉跄着后退两步,
眼神里的疯狂几乎要溢出来,“沈砚!他救过我的命!当年在清水河边,
要不是他把我从水里捞上来,我早就淹死了!这份恩情,我欠他一辈子!现在他就要死了!
就在我眼前!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他死吗?你要我变成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
”清水河……溺水……救她的人?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一股腥甜的铁锈味弥漫上来。那个冰冷的冬日下午,刺骨的河水,
我拼尽全力拖着她游向岸边,自己肺部呛水差点窒息的感觉……清晰得如同昨日。
而那个所谓的“救命恩人”陈默,当时不过是在岸边惊慌失措地喊了几嗓子,
甚至在我把人拖上来后,才假惺惺地凑过来。她竟然一直……一直以为是陈默?
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被彻底否定的悲凉,瞬间淹没了我。我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感觉无比陌生。五年的朝夕相处,抵不过她心中那个被美化了无数倍的幻影。“所以呢?
”我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所以,就要用我的命,
去还你的‘恩情’?”“什么叫你的命?!”林晚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彻底炸了,“十年!
就十年!换你五十年不够吗?沈砚!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么冷血!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她嘶吼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精致的妆容早已花得一塌糊涂,
只剩下狰狞的底色。自私?冷血?我看着眼前这个为另一个男人哭得肝肠寸断的妻子,
心一点点沉下去,沉入不见底的寒潭。原来在她心里,我是这样的存在。
客厅里只剩下她粗重的喘息和压抑的抽泣。死寂如同冰冷的潮水,蔓延开来,
几乎要将人溺毙。窗外的混乱喧嚣似乎也远去了,只剩下这令人窒息的僵持。
就在我以为这场闹剧要以她的崩溃收场时,林晚突然动了。她不再看我,而是猛地转身,
冲向了卧室。很快,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深蓝色的、印着烫金徽记的硬质文件夹,像一份重要的合同。我认得它,
那是我们结婚时,在“生命管理局”登记处签署的《婚姻生命共同体绑定协议》的副本。
当时只觉得是个象征性的、浪漫的仪式,象征着彼此生命共享、荣辱与共。谁也没想到,
在倒计时降临的今天,它成了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林晚拿着那份协议,
一步一步走回客厅中央。她的眼神空洞而绝望,却又燃烧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火焰。
她停在我面前,隔着几步的距离。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血液瞬间凝固的事情。
她举起那份沉重的硬质文件夹,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地砸向茶几上那只她最喜欢的、价值不菲的水晶烟灰缸!“哐当——哗啦!!!
”刺耳的碎裂声在死寂的房间里炸开!晶莹剔透的碎片如同冰雹般向四面八方激射,
散落一地,在灯光下折射出冰冷而尖锐的光芒。下一秒,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林晚毫不犹豫地、直挺挺地朝着那片布满尖锐碎玻璃的地面跪了下去!“噗通!
”膝盖撞击地面的闷响,伴随着玻璃碎片被碾碎的细微“咔嚓”声,
清晰地敲打在我的耳膜上。“啊——!”剧痛让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
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睡裙下摆瞬间被染红,点点猩红在浅色布料上迅速晕开,
如同雪地里绽放的残酷花朵。她的脸因疼痛而扭曲,冷汗瞬间浸湿了鬓角,嘴唇被咬得惨白。
可她死死地撑着,没有倒下。她抬起头,布满泪水和汗水的脸仰望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最卑微的乞求,也带着一种疯狂的、不容拒绝的逼迫。
“沈砚……老公……”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混杂着痛苦和绝望的哭腔,
“我求你……求你了!就匀给他十年!用绑定协议转移!法律允许的!
我求你……就当我求你了!”她跪在玻璃渣和血泊里,如同最虔诚的信徒,
又像最无助的囚徒。她伸出那只没有沾染血迹的手,颤抖着指向那份被她摔在地上的协议。
“签了它……救救他……也……救救我……”她泣不成声,
身体因为疼痛和激动而不住地痉挛,
“不然……不然我这辈子……下辈子……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也永远……无法原谅你!
”空气仿佛凝固成了沉重的铅块,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肺部撕裂般的疼痛。林晚跪在那里,膝盖下的血渍在浅色的地毯上晕开,
像一幅绝望的抽象画。玻璃碎片刺破皮肤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荡,
混合着她压抑的、痛苦的抽泣。那份深蓝色的《婚姻生命共同体绑定协议》静静躺在地上,
离她的血泊只有几寸之遥。烫金的徽记在灯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像一个无声的嘲讽。
五年婚姻,荣辱与共的誓言,最终成了她刺向我的刀。我看着她惨白的脸,扭曲的痛苦表情,
还有那双死死盯着我、充满了疯狂乞求和孤注一掷的眼睛。心口那个地方,
最初被攥紧的剧痛,此刻已经麻木了,只剩下一种空洞的冰凉,如同被挖走了一块。“好。
”我的声音响起,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像深潭不起一丝波澜的水面。林晚猛地抬起头,
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混杂着狂喜和一种解脱般的虚脱。她的嘴唇翕动着,
似乎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我没再看她,径直绕过那片狼藉的玻璃和血迹,
走到沙发前。弯腰,捡起那份沉重的协议,
纸张的边缘似乎还残留着她刚才紧握时的力度和温度。翻开,直接翻到转移附加条款那几页。
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严谨而冰冷。我拿起茶几上那支她平时用来画设计图的钢笔,
笔尖悬停在签名处。“十年?”我侧过头,目光落在她身上,不带任何温度地确认。“十年!
”她用力点头,生怕我反悔,声音嘶哑却急切,“十年就够了!沈砚,
十年对你来说……”“够了。”我打断她,声音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十年?
六十年减去十年,还剩五十年。一个漫长的、失去意义的数字。
我用笔尖点了点协议上“转移年限”的空白处,“这里,你填十年。受益人信息,
”我的笔尖移到另一个位置,“填陈默的全名和身份ID,别弄错。”林晚挣扎着想站起来,
膝盖的剧痛让她又跌坐回去。她顾不得许多,几乎是爬着挪到茶几边,从我手里夺过笔。
她的手指抖得厉害,笔尖几次戳破了纸张,留下难看的墨点。她低着头,
无比专注地、一笔一划地填上“十年”,然后飞快地写下陈默的名字和那一长串数字,
动作带着一种病态的急切,仿佛慢一秒,那个男人的生命就会在她指缝间溜走。填完,
她像是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整个人虚脱般靠在茶几腿上,
把协议推到我面前,眼神里充满了急迫的催促。我接过协议,目光扫过她填写的部分。十年。
陈默。身份ID无误。最后,我的视线落在签名栏下方,
那几行被刻意设计成与背景色几乎融为一体的、极小字号的附加条款上。其中一条,
如同潜伏的毒蛇:>转移方同意,在转移指定年限生命时间的同时,
年限内相关联的、由转移方自主选择的特定记忆片段需在转移时于系统内进行锚定确认。
此记忆片段将完整覆盖植入受益人原有相关记忆。
我的指尖在那个“特定记忆片段”的条款上轻轻划过。然后,拿起笔,
在签名栏旁边那个不起眼的“记忆锚定点选择”电子屏上,
飞快地输入了一个精确到秒的时间坐标——**2017年12月15日,
下午14时28分至31分**。那是清水河边,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寒风,
我拼尽全力托起她下沉的身体,肺部呛水火烧火燎的窒息感……清晰如昨的绝望三分钟。
确认。选择完毕。没有丝毫犹豫,我在协议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沈砚**。
笔锋稳定,力透纸背。最后一笔落下,手背上那串蓝色的倒计时数字猛地闪烁了一下!
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身体里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被瞬间抽离的感觉袭来,
让我眼前微微一黑,脚步虚浮地晃了晃。与此同时,我清晰地感觉到,
了飞快的跳动:**60年** → **50年 00天 00时 00分 00秒**。
定格。几乎在同一秒,林晚手腕上的个人终端发出了清脆的提示音。
她迫不及待地抬起左手手背,
看着上面陈默的倒计时状态瞬间刷新:**接收生命时间转移:10年。
****当前剩余:10年 00天 00时 00分 00秒。**“成了!成了!
阿默有救了!”林晚爆发出一声狂喜的尖叫,泪水再次奔涌而出,但这次是纯粹的喜悦。
她挣扎着想站起来,膝盖的伤让她疼得龇牙咧嘴,脸上却绽放出劫后余生般灿烂的笑容。